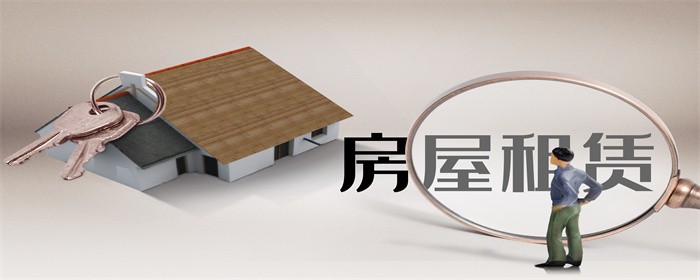一个几乎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大党,却凑不出千分之一的信仰
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政党,能像苏修后期那样,把“信仰”这两个字玩到如此抽象的程度。
一千多万、将近两千万党员,摊开来看,差不多占了成人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个规模,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庞然大物。照理说,这么多“先锋队成员”聚在一起,思想的火焰哪怕不至于燎原,也该把空气烧热一点。
结果没有。
不仅没烧热,反而冷得出奇。
文件越来越厚,口号越来越整齐,会议越来越严肃,可一旦绕开纸面,问一句最简单的问题:“你信的到底是什么?”
空气立刻开始结冰。
信马克思?那太抽象了。
信共产主义?那太遥远了。
那信什么比较稳妥?信组织、信流程、信既有秩序,最好再顺便信一信个人前途。
于是,一个以革命起家的党,慢慢变成了一个管理革命遗产的机构;一个本该不断怀疑既有权力结构的组织,开始把“稳定”当作最高美德。而真正的信仰,被请进文件里供着,却被请出现实生活。
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这个党的人数越多,真正敢讲阶级、讲剥削、讲方向问题的人反而越少。不是因为问题不存在了,而是因为讲问题的人显得不合群、不成熟、不会看大局。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的环境里,往往是最不受欢迎的一类人。他们太认真,太容易把话说到根子上;他们不太懂得“阶段性正确”,也不太擅长用模糊语言替现实开脱。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荒诞而稳定的状态:
口号越来越响,信仰越来越轻;
组织越来越庞大,思想越来越空;
文件里全是“人民”,现实中却处处避开人民。
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恰恰不需要信仰来维持运转。
它需要的是合格的执行者、稳妥的解释者、熟练的表态者。
至于信仰——有当然更好,没有,也并不影响流程继续。
于是,党员数量逐渐成了合法性的装饰品,马克思主义成了引用率极高、实践率极低的经典文本,共产主义则成了被不断推迟、不断“再讨论”的未来概念。
如果真要统计“有多少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那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因为信仰不是登记表,不是党龄,也不是宣誓录像。它只会在一个人面对现实压力、利益诱惑和立场选择时,短暂地露面。
而恰恰是在这些关键时刻,很多人选择了沉默、回避、顺从,甚至反过来嘲笑那些“还在当真的人”。
所以说,这一切确实有点可笑。
不是马克思主义可笑,也不是共产主义可笑,而是一个号称掌握真理的庞然大物,最终却对“当真”这件事保持着高度警惕。
一千九百万党员,哪怕退一万步讲,其中只有千分之一还保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那也该有将近两万人。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两万人,足以形成稳定的理论圈层,足以在关键节点发出不同声音,足以在路线发生根本转向时制造阻力、撕裂,甚至公开对抗。
历史上从来不缺这样的例子。
列宁时代,党员不过几万,处境比后来任何时期都要艰难得多:流亡、分裂、镇压、失败轮番上阵,但路线斗争从未消失,原则问题从不含糊。正因为那时的党小,却有信仰密度,有理论锋芒,有一批人是真的把立场当成命。
反过来看苏修末期的崩塌,却几乎没有出现像样的内部抗争。没有成体系的理论反击,没有大规模的路线争论,更没有以信仰为名的公开决裂。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令人错愕的顺滑:集体沉默、迅速转身、统一改口,仿佛过去几十年的信仰只是一套工作话术,用完就可以随手丢进抽屉。
这说明问题从来不在“敌人太强”或“外部压力太大”。
如果内部真还有哪怕千分之一的信仰者,这种解体都不可能如此体面、如此安静、如此配合。
崩溃,本该伴随着痛苦、撕裂和抵抗。
而当一切只剩下交接、表态与重新站队,那只能说明:信仰早在崩溃之前,就已经被清空了。
历史并不苛刻。
它并不要求人人都是殉道者,
它只要求,在关键时刻,别所有人都同时选择放下。
当一个党里,“有信仰”变成一种风险,“没立场”反而最安全,那再大的规模,也只能说明一件事:
信仰,已经从方向盘,变成了装饰品。
这不是敌人的胜利,这是信仰在内部被长期消耗、透支之后的自然结果。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