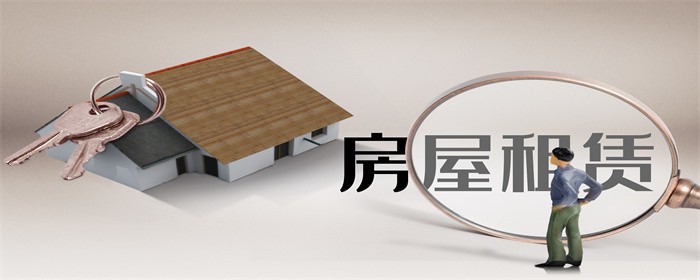妇女运动的新崛起 | 二、导致这种崛起的因素是什么?

二、导致这种崛起的因素是什么?
(一)前一波运动的收益
新一代能够以一种叠合不平衡方式从前几波妇女运动的成就中受益:首先,在正式权利、家庭和法律法规的变化、妇女获得教育和健康方面,其次,在生育和性的权利和自由方面,第三,在专业、学术、文化、政治和媒体世界的开放中。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女性主义派别已经成功地活动于劳工运动中并与之一同抗争,以改善劳工权利。
(二)劳动力的女性化
在世界各地,女性工作时长都超过男性……但她们的部分工作是无形的:在全球南方和北方,女性继续付出世界无酬照顾工作的四分之三以上。
虽然女性在就业率上与男性相比仍有差距,但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全世界每十名工人中就有四名是女性。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这种增长,虽然北非和西亚等一些地区的百分比(低于30%)低于全球其他南方地区。
在世界各地,女性都更有可能被迫从事兼职工作,这一趋势随着Covid-19大流行而加剧。这种低水平就业人数可能占到女性就业总数的一半。在全球范围内,近一半的女性工人处于国际劳工组织所称的“弱势就业”领域,尤其是在农业企业、手工业和贸易行业。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比例超过70%。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深刻改变了经济和就业结构
总体而言,过去二十年来,就业已经从农业转向工业,然后转向服务业,服务业雇佣了约一半的劳动力。
全世界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工作,农业仍然是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主要的从业行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农村女性化现象日益严重。由于进入城市的产品有60%以上是由家庭和农民农业生产者生产的,因此妇女对经济至关重要。但经济政策有利于以牺牲当地消费为代价的出口导向部门,而其中的劳动者主要是男性。由于女性占世界小农的大多数,所以她们的处境依然很脆弱。
自1995年以来,工业从业者中女性人数有所下降。一般而言,她们集中在纺织和服装等部门。在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出口行业雇佣了大多数女性,而且这些女性往往非常年轻,而且工资低、缺乏社会保障、工作条件差,并面临性别暴力。
从1995年到2015年,女性在全世界的服务业从业者中占主导地位。女性集中在某些活动领域:中等收入国家的贸易、高收入国家的卫生和教育。总体而言,女性在服务业中的高比例就业和高频率的兼职工作同服务业中相对较低的工资有关,尤其是在销售、清洁和餐饮等行业。女性过度代表着健康、教育和社会工作,与贬低这些领域所需技能的性别成见直接相关。
但更一般地说,“灵活就业”和特殊困难条件,包括执行多种任务和情感参与的能力,需要塑造新式奴性的“典型的女性特质”。
全球平均而言,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估计为23%。近40%的女性由于工作原因没有参加社会保障计划:在非正规部门或未申报的岗位工作,黑人劳工,在做临时工、居家工作等等。结果是,二亿达到退休年龄的妇女根本没有养老金。全世界共有70%的贫困人口是女性。
大流行期间,大量使用远程工作将家庭、有偿工作和家务劳动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增加了女性的身心负担。许多女性因工作过度劳累而被迫辞职、被解雇或被阻止工作,从而被剥夺了独立生活的手段。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统计数据来充分评估这会怎样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但我们可以肯定,现有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了。工作的“女性化”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参与者的增加,也意味着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女性特有的工作条件(危险、不稳定、脆弱、未充分就业、缺乏权利和社会保障、工会化率低)往往会扩展到整个无产阶级。
就业的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几乎占总就业的一半,非正规经济的份额也是如此——涉及十分之六的工人。
有偿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以及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活之间的界限往往会变得模糊——就像在再生产工作中一样(你必须每天二十四小时为老板服务)。这意味着使用女性化的能力和特征,例如利用女性有吸引力的存在、诱惑、关系中的关怀、同理心、处理多重任务等来为公司服务。
(三)性别暴力的增加
针对女性的暴力由社会建构,然后由国家正常化,且不受惩罚。暴力导致的死亡发生在歧视和剥削妇女的复杂网络中,可按性别、阶级、种族、复杂的危险情况、边缘化、不安全、军事化、移民等因素分类。
全世界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在生活中会遭受性暴力或身体暴力。在性别暴力行为中丧生的大多数妇女是被伴侣或前伴侣杀害的。自2008年危机以来,基于性别的犯罪进一步升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遭到破坏,妇女的照顾责任和任务增加,逃避暴力的机会减少,而紧缩政策削减了为女性受害者提供的中心和庇护所的资金。年轻女性在经济、心理和性方面日益独立,使她们成为男性家人“报复”的对象。仇恨犯罪“纠正”“背叛”保守守则的女性、女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行为,被右翼政治和宗教舆论制造者合法化。
杀害女性,在今天被认为是极端形式的性别暴力之一,由多种形式的暴力导致女性被谋杀和死亡,仅仅因她们是女性:身体的、性的、心理的、家庭的、劳动的、制度的。杀害女性的暴力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起注意,于1993年在墨西哥华雷斯城被记录下来;随后在墨西哥全国进行了追踪,现在被认为是一种全球现象和拉丁美洲的区域现象。“一个都没有!”(Ni Una Más!)是墨西哥妇女提出的口号,二十二年后成为阿根廷妇女的口号“一个也没有”(Ni Una Menos)——今天已流行于全世界——是这种厌女症和男子气概暴力形式,及有罪不罚和侵犯人权持续存在和增加的明确证据。许多国家的妇女组织起来寻找失踪的女儿,并在杀害女性的案件中要求国家伸张正义。以受害者的名义,这些运动往往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例。
在美国引爆的MeToo运动产生了全球影响。妇女公开谴责不同文化、专业和社会领域的性骚扰和工作中的性骚扰,从而打破沉默,同时在正式框架中展现她们这样做时面临的障碍,并开始确立公开谴责的合法性。
新一代青年女性主义者通过反抗大学当局并要求应对性侵犯的反应和机制来回应大学中的性暴力。
在许多国家,妇女因被拐卖和被国际有组织犯罪网络用作性奴和强迫劳动而失踪。在很多冲突中,强奸被用作战争武器。这背后有多种动机,从社区羞辱到种族清洗和恐吓平民。
妇女移民的条件使她们更容易成为性暴力、失踪、卖淫、拐卖、勒索、与家人分离(许多人带着孩子迁徙)、任意羁押、疾病、事故和杀害女性的受害者。由于她们经常要对与之一起迁徙的孩子负责,使他们成为双重目标,且困难增加,因为他们作为无证工人的身份使她们与孩子更难就业或获得服务。
过去二十年里,在要求国家担负责任并建立新的法律框架来应对暴力的女性主义运动的压力下,许多国家立法并出台公共政策来对抗不平等,解决妇女遭受暴力侵害和杀害女性的问题。然而,在实践中,这些政策并没有获得充分的资助或得以真正实施,更不可能根除暴力,政府的行动与其话语相矛盾。相反,暴力在增加,同时女性谴责暴力的意志和决心也越发明确。
遭受暴力的女性在诉诸司法时面临的障碍同性别歧视、认为女性劣等的偏见和维持系统的文化和观念的刻板印象等有关。为保护遭受暴力的女性受害者而斗争的女性活动者、人权捍卫者和女性主义者面临敌意和被定罪的威胁,在某些时候还被迫流亡。
(四)妇女在社会和社会运动中作用的增加
妇女一直是挑战既定秩序的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近几十年来,作为政治主体的女性明显出现在各种动员的最前沿。
仅举几例:马克西玛·阿库纳(Maxima Acuña)和她在秘鲁反抗采矿业的斗争;贝尔塔·卡塞雷斯(Berta Caceres,2016年3月被武装人员杀害——译注),洪都拉斯的环保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阿拉·萨拉赫(Alaa Salaah),苏丹民主起义领袖;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帕特里斯·库洛尔斯(Patrisse Culors)和奥帕尔·托梅梯(Opal Tometi),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活动者;格蕾塔·通贝格(Greta Thunberg,瑞典青年环保运动者——译注),全球青年反对气候变化运动活动者;达亚玛尼·巴拉(Dayamani Barla),在印度贾坎德邦领导群众动员反对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al);马赛妇女牧民委员会(Maasai Women’s Pastoral Council),领导洛里昂多的土地斗争;“团结与积极妇女”(Mujeres Unidas y Activas (MUA)),旧金山湾区拉丁裔移民妇女的草根组织,在2013年批准家务工人权利法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妇女领导着社区抵抗,例如在巴西,要求保护一百多个土著族群的土地、健康和教育权的妇女游行;或在厄瓜多尔,对试图终止燃料补贴、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经济措施感到愤怒的运动中,土著妇女起领导作用。加拿大第一民族(指土著民族——译按)妇女和美国原住民妇女已设法停止开采其领土内的自然资源。
智利的青年女性和学生参与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抗,他们通过推翻皮诺切特宪法,揭示了新自由主义的模范国家完全就是个谬误。特别是“8M女性主义协调员”(8M Coordinadora Feminista),通过其组织集会和制定女性主义纲领,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领导反暴政和反社会崩溃运动的妇女被迫与渗透社会和国家机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在巴西和美国,妇女一直站在抗议政府对大流行的灾难性处理的最前沿,两国政府由男子气概和专制的总统博尔索纳罗与特朗普领导。
在前苏联集团的两个国家,妇女正在领导人民群众反对专制和腐败政权的斗争。在波兰,他们通过挑战对堕胎权的限制而动员起数百万人,为普遍成长为民主要求创造了空间。在白俄罗斯,他们站在民众斗争的最前沿,要求尊重投票结果并赶走篡位的政府。
新的女性主义热潮和妇女在社会运动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使新型女性政治人物的出现成为可能。举一些例子:阿达·科劳(Ada Colau,巴塞罗那的首位女性市长——译注)和我们的同志特蕾莎·罗德里格斯(Teresa Rodríguez,西班牙反资本主义者和前进安达卢西亚(Adelante Andalucía)成员——译注)在西班牙的选举,美国民主党左翼的新(非白人)发言人,如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 Cortez,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成员,民主党国会议员——译按)和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党成员,巴基斯坦裔,民主党众议员——译按),或巴西的玛丽埃利·佛朗戈(Marielle Franco,巴西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和第四国际巴西支部反叛派成员,里约热内卢州议员,2018年被暗杀——译按)和她的搭档莫妮卡·本尼西奥(Monica Benicio,社会主义与自由党成员,里约热内卢州议员)。
因此,妇女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中的积极作用和领导作用显著增长,充分参与国家政治进程,抵制新自由主义政策让广大人口陷入贫困的行径。
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实际上是与保护生命、生态、经济、社会、文化,有时甚至是精神意义上的社会再生产问题相关的斗争。这些运动与主要参与者对自身环境及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和父权制暴力的认识的提高齐头并进。

(五)新浪潮的国际先行者
在前一波妇女运动中,有一些国际协调。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堕胎权利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Abortion Rights)成立,并演变为后来一直都活跃的全球妇女生育权利网络(Women’s Global Network for Reproductive Rights)。1981年在哥伦比亚举行了第一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女性主义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11月25日定为“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日”,联合国于1995年将其定为“消除暴力国际日”。
“世界妇女反贫困和反暴力大游行”开始于1995年北京联合国妇女大会之后的1998年,这次大游行受到同年魁北克妇女大游行的启发,针对草根妇女和街头行动提出了17项要求和建议,以消除贫困和对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该活动在社会论坛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且在一些国家仍然存在。
与这些国际协调的努力相伴的,是国际上雄心勃勃的社会运动兴起的时刻,这些国际协调也与这些运动一起遭遇了相同的衰落。然而,尽管非政府组织化(NGOization)有负面影响,但这种结构使一定的国际协调得以继续。就粮食主权问题举行了农村妇女国际会议(Nyeleni - Mali 2007);以及主要国际农民网络“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日益明确的女性主义定位。
与此同时,近几十年爆发的所有社会起义或革命都见证了妇女的积极参与,她们在运动中制定自己的分析和行动框架:从萨帕塔运动的妇女法到“阿拉伯之春”,妇女出现在开罗解放(Tahir)广场、占领运动、西班牙愤怒者运动(15M)等运动中,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库尔德女战士的惊人战斗。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不再是优先考虑斗争、反殖民、反资本主义、民主、反种族主义和反父权制的问题,而是开始清晰地显现一种以综合方式处理所有压迫的交叉女性主义。
(六)其他女性主义流派
在战后繁荣时期经历过一定程度福利制度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女性主义已成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副产品。
改良主义女性主义的特点是将女性主义要求和活动者纳入社会民主党及其他改良主义政党之中,特别是当她们参与地方或全国政府时,为受妇女运动启发但很少或缺乏自我组织的方案实施相关政策,并提供资金与组织。紧缩政策几乎没有为这种女性主义留下空间。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侧重于企业、行政部门和主流文化的女性化,而不质疑主流文化的阶级和种族性质,相反,它为剥削其他社会阶层(移民、种族化群体、穷人)而辩护:……这种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女性主义抵制认同女性主义的新一代和其他非特权女性。
在全球南方,“非政府组织化(NGO化)”现象发展起来了,即在非政府组织(NGO)内部和联合国会议框架内,协调妇女运动并使之逐渐温和,非政府组织通过资助妇女运动并使之专业化,损害了妇女运动的激进性和自我管理。
以生理决定论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的迅速崛起,在限制跨性别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反动运动中最为明显,这是另一个有问题的障碍。
(待续)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